他是一位谦虚朴实、待人接物随和、淡泊名利的导师,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学生的关爱和热诚。他是一名让学生充满了敬重感的导师,是一位将学生视为孩子的“家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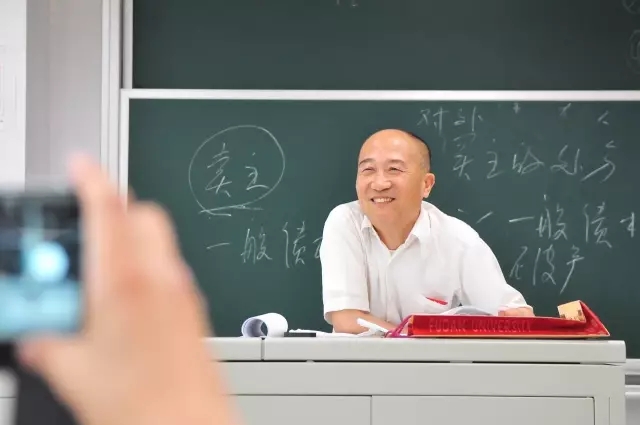
导师简介:
段匡,1952年生,东京都立大学民法学硕士、博士课程毕业。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运用民法解释学方法研究民法中的疑难问题。代表作:《日本民法解释学》,译著:《英美判例百选》《现代民法基本问题》。
育人理念:
教学相长,对于老师而言,学生的进步就是最大的回报。
忠厚长者,高山仰止
刚入学时,总会有同学问我“你老板是哪位啊?”事实上,我非常反感这个问题,甚至有些不可理解。为什么会有学生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并且这种称呼能在大学校园里大行其道呢?或许是当下的社会,人已经浮躁到用商业关系来衡量一切;或许是这十里洋场,经济观念早已渗透人心;也或许是在这个一切都可以解构的年代,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感也已受到侵蚀和淡化。学生们用一个“老板”的戏称,便恰到好处的形容了和导师的关系。可是,师生之间的关系用老板下属关系来类比是否适合呢?导师应该是一位学者,而不是一位商人,在自己学有所成的同时,不仅要不断钻研自己领域的学问,还要尽可能地拓宽视野,并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他们最初走上科研道路时,为他们指引方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身为范,段老师便是为人师表中当之无愧的楷模。段老师桃李满天下,但在他一届届的学生里,却很少有人戏谑地称其为“老板”。提起他,学生们无不恭恭敬敬地尊称一句“老师”。他是良师,也是益友。在师从段老师的日子里,我由衷地想尊称他一声“先生”。

经师易遇,人师难求。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中,段老师始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着他的每一个学生。课堂上,他能深入浅出,将艰深晦涩的民法理论讲得浅显易懂;生活中,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学生的关怀总是看似平淡却又深入心田。段老师乐于与学生们分享他的一切,不惟知识,还有许多珍贵的人生体验。而学生们也喜欢向段老师请教,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会寻求他的帮助。法学院博士生举办讲座,需要老师点评,大家第一时间想到了段老师。学生申请出国需要找老师写推荐信,大家还是会找到段老师。对于这些请求,他总是笑眯眯地答应下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学生。但是,如果有人向他提出违背原则的要求,他便会义正言辞地加以拒绝。这样的段老师,学生又怎会不尊敬呢?
在校园里,曾有同学知道我是段先生的学生,就过来问我:“段老师这学期什么时候有空啊?我们很想去拜访老师。”还不待我回答,他便急切地说起来:“虽然段老师只给我们上过一个学期的课,但是我们班的同学都特别想他,所以想找个时间能和段老师再好好聊聊。段老师的课,总是能让我们在笑声中把知识消化,过去这么长时间,那种课堂氛围我却一直忘不掉。”我想,像先生这样学识渊博且风趣幽默的老师,学生们怎么会不喜欢呢?
段老师爱笑是出了名的,每每见他,他都是笑容可掬,让人倍感亲切。博士班的同学里不少是段老师面试的,他们总是跟我说,复试的时候段老师温和的笑容,给了他们很大鼓励。在微笑的背后,是先生淡泊名利的内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许多人总是将金枷套颈,玉锁缠身,汲汲于名利富贵,从而忘却初心。“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像先生这般放下功利心,能保持内心的安宁的人,又怎会不快乐呢?

在名利面前,段老师淡泊宁静,但是对于后辈的成长,他尽心尽力,不辞辛劳。“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但作为段老师的学生,我也清楚先生有着格外严厉的一面。入学第一次见面,段老师就劝诫我应当勤勉于学术,切勿虚度光阴。博士三年,如白驹过隙,时不我待,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要将心真正沉淀下来,埋心于书堆中,真正学有所得,莫待他日后悔莫及。入学后,他亦总是挤出时间督促我们学习,跟踪我们的进度,组织我们集中交流,指导我们的科研工作。
除此之外,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值得我等学子仰望。34岁东渡日本,在日苦修十年,段老师深知时间的宝贵。文革期间,先生曾一边卖酱油一边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他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学生珍惜学习机会,好好读书。过往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的社会与日俱新。在求学机会日益增多的今日,很多同学却并未真正明白时间对于他们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读研读博只不过是目标不明之下的缓兵之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适合做什么,也没有做好走进社会的准备,于是便盲目地希望能够在学校多享有片刻的宁静,希望老师能够把自己的路子定下来。当下许多学生的盲目和困顿,是段老师最为担心并痛心的。蔡元培先生于北大就职时,曾发表演讲,“诸君肆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世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光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先生的忧虑,恐怕也不只是段先生之忧,而是为天下所有认真学术的老师忧虑吧!
临乱世而继绝学
很多人不理解,段老师为什么总是能够“淡看世事去如烟”,他淡泊名利,生活俭朴,有时候一日三餐可以在食堂里简简单单的解决,但他不容有人在学术上有一丝一毫的懒惰和懈怠。在先生对学生的传道授业中,不仅包含着他那一代中国法律人对下一代法律人的关怀与期许,还包含着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对下一代的殷殷之情。

段老师的治学经历也是中国法治发展的一个缩影。有一天,我在江湾校区的食堂里偶遇段老师,闲聊之间,我提起近几年来复旦大学图书馆外文资料越来越丰富了。段老师沉默良久,轻轻地感叹了句,“能在这样的时代学习真是幸福”。平淡的话语后掩藏了过去的多少辛酸和苦痛?那一刻,我也只能沉默。法理学家李步云教授在一次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法治历程的会议上,失声痛哭。这一份悲戚又何尝不在我们每一位中国法律人的心中呢?
段老师这一代法学家是生逢激变的一代。出生时即遭遇新旧法统变革,初中毕业又遇到上山下乡。艰苦卓绝的生活没有阻挡这代人求学的决心。1986年,段老师东渡日本,而那个时候,复旦大学法律系才恢复不满三年。我不知道段老师负笈日本之后,在日本时看到日本法百年发展赓续的灿烂时是怎样的心情,也不知道段老师在东京寂静的夜里翻阅我妻荣所著的《民法讲义》时的是怎样的心情。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数代人传承积淀方得进步,然而法学的这种传承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被迫中断,此中艰辛恐怕很难为外人理解。很少有人能明白,在浩劫之后,我们法律人面对的是怎样一片残垣断壁,而这份重建的重任就落在了段老师这一代法学家的肩上。留日之前,段老师下定决心,“此去东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他的无奈,他的离愁,还有他高远的志向,均化为他十年异国求学的动力。

段老师那一代法学家,是重建的一代,是在毁灭中再造的一代。尽管求学之路无比艰辛,但是他却毫无怨言,对于祖国的爱,对于法治的信念从未磨灭过半分。我们这一代学子是幸运的,因为有段老师这一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我们已无需再体会面对一片残垣断壁的荒凉,也无需再在黑暗泥淖之中举步维艰。不知道有多少次,律师、法官们在知道我是段老师的学生之后,告诉我说,在自己还不知道民法为何物时,是段老师的《日本的民法解释学》给我指明了方向,而自己正是站在这个台阶之上攀登。
段老师的研究领域是通过民法解释学解决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法学方法论日渐成为显学的当下,方法论的著作汗牛充栋,各种关于方法论、乃至方法论的理论喧嚣尘上。但是真正理解方法论之于法学的意义的又有几人呢?自历史法学派仿造自然科学创造法学一词以来,法律学习者自认为法律也可以像自然规律一样严谨科学。与之相对应,德国检察官基尔希曼在1874年柏林法学会上作了《作为科学的法学的无价值性》的演讲无疑是对洋洋得意的法学家们的当头棒喝。随着而来的也是长达100多年的大争论,法学究竟是科学么?如果法学是科学的话,又是怎样的一门科学?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耶林,还是拉伦茨都无法置身世外,其希望通过法学方法论这一手段回应基尔希曼的质疑。也许是机缘巧合,在100多年以后,段老师通过他在日本的研究,同样对这一问题做了回应。在段老师看来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法学是通过一个大家都能公认的、共识的制度,在这个制度框架下怎么样使得这个制度一步步地能够达到它原先希望达到的目的,而通过方法论的运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判断。它的研究和理论,为无数人指明了方向。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数十载的民法研究中,段老师也早已把民法的价值序列贯彻在一言一行中,学问的传承,不仅仅在于著书立说,也在于平时的点滴之间。在民法的价值判断中,平等自由总是处在优先地位。段老师也说:“民法学者总是特别的谦虚,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而在民法的研习过程中,你会发现民法的世界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抽象的法律尚且如此多元,何况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呢?而我们每个人不过是这千千万万大众中的一员。”在宏大的叙事背后,并不是对个体多样性的抹杀。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每个个人在这个复杂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也就自然而然会变得谦虚。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尽到自己相应的责任。鲁滨逊在孤岛上一个人生存时并不需要秩序,但是这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现代社会是一个人与人的社会,人与人的社会中需要秩序,这种秩序需要通过法律等加以建立,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每个人的自我约束。在一次校外访谈中,段老师指出,对于法律人而言,不仅仅需要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要把这部分东西贯穿到自己的行为中去。段老师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在教授民法之余,段老师也教授环境法,在环境法的课堂上,他不仅仅介绍最前沿的环境法发展动态,也将环保理念传递给每一个学生。段老师很早就开始用环保袋,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将家里的电器更换成具有节能功效的,事情虽小,却是对他将知识运用到生活中这一理念的最好诠释。
“高山水深斯人不出,云情霞想其志可知”,无须多言,在段老师平时的一言一行中,已然让我们体会到一个名师的风采。
导师访谈:
问:段老师,您获得过的荣誉不计其数,“心目中的好导师”这一奖项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么?
答:这个奖项肯定是和别的奖项是不一样的。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奖项是由学生评选的,其中没有行政的色彩,或者说行政的色彩比较淡。到现在为止,我带的博士里已经毕业的已经有6个,而带过的硕士、上过课的本科生就更多了。这个奖项是学生们给我的肯定吧。我一直觉得教学相长是非常重要的,好的老师也需要有好的学生。我认为法学教育里,老师的作用可能只能起到1/3,剩下的2/3需要学生自身努力,学生的努力对于老师来说,也是很好的激励。
问:段老师,您在日本留学多年,有没有发现日本法学教育有什么特色?
答:我是1986年9月去的日本。当时我是随我夫人去日本的,我的夫人在庆应大学读法律本科,借着这个机会我也间接学了一些本科的课程。在日本时,我先学了一年半的日语,然后在东京都立大学读了一年的研究生,日本的研究生是预备性质的,没有学位。然后,我又在东京都立大学读了硕士和博士。日本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日本是一个继受法国家,它本身不是创造这些法律的国家,而是从国外拿来的,所以在学习上,它非常开放。我个人认为,去日本学习法学是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像如果你去德国,德国是成文法的代表,德国学者肯定会认为德国法好,而如果你去美国,美国是判例法的代表,美国学者肯定会认为美国法好。但是如果你去日本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日本法来说,德国法、美国法都是学习的对象。而且日本法律教学比较偏重于理论体系的教学,会把日本法每个条文的来源,也就是说,每个条文是从哪个国家继受而来的,讲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在日本学习法律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学习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
问:现在我们都知道民法方法论非常重要,但是当时的话可能大家普遍关注具体制度层面更多一点,那么当时段老师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法学方法论这块内容呢?
答:这也算是一个巧合吧。九十年代初,当时梁慧星老师在日本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民法解释学对于中国民法发展很有价值。所以,梁老师提出,由他负责写总论,而我写一些日本的资料。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大的意义。中日同属东亚文明,民法这套法律制度,是原来中华法系所没有的,这一点日本和中国是一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从大陆法系继受了民法制度。在这样的继受之后,日本的民法解释学解决了几重的问题。第一,如何把民法体系化,以及如何与日本原有的传统整合的问题。日本传统上的各种习惯如何融入到西洋的民法中,这也是法治发展的重要问题。民法的条文是极其抽象的,但是在适用中必须还原到具体,而在这些适用中,又可以发展成的新的立法,这其中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第二,我们说民法学就是民法解释学。民法的条文是千千万万社会生活现象的抽象,在具体的法条适用中必须将条文与具体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因此,也必须有这样一问科学。第三,我觉得法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类似于工科的科学。法学和政治学不一样,我想法学需要一个大家可以公认的、可以达成共识的制度,这个是法学科学性的一个方面。此外,法学并不能只是一个语言游戏,法学科学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如何将法律价值观贯彻到法律中,法学中也应当存在价值判断的因素,我也不希望学生学习法律,最后只是成为一个适用法条的机器。
这些经验对于中国现在的法治发展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问题,在立法上,现有的法律缺乏体系性与统一性。这些就需要通过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去加以合理的解释,才能正确的适用法律。






